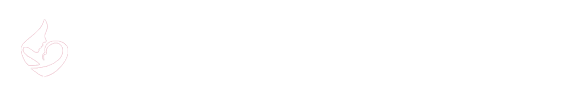全国服务热线:0898-08980898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 地址:
- 海南省海口市
- 邮箱:
- admin@youweb.com
- 电话:
- 0898-08980898
- 传真:
- 1234-0000-5678
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及其限制添加时间:2025-08-14
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余万里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出口管制政策是美国为维护国家安全、推进对外政策时经常运用的经济手段之一。在
中美关系发展的历程中,出口管制始终是一个被列入双边高层日程表的重要议题,并且对
双边的政治、经济、贸易的发展构成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本文试图结合美国出口管制政
策的演变、基本状况以及美国对华管制政策的发展变化,对该政策在中美关系中的影响作
用、发展趋势及其制约因素作出初步的阐述和分析,同时也为国内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提供
基础性的参考。
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演变
美国出口管制的源起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1940年7月美国国会授权总统出
于国防利益的需要,禁止或削减军事设备、产品、工具、原材料或技术服务的出口。二战
结束后,美国又面临着与苏联社会主义集团对抗的冷战局面,出口管制政策因此继续延续
下来,并且不断得到强化。194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部《出口管制法案》(the Export
Control Act of 1949),使战时临时性的出口管制措施固定化和永久化。该法案规定美国
出口管制的主要目的是两个方面:一、控制具有军事用途的商品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输
出;二、防止短缺商品外流。
1949年的《出口管制法》实行了20年,到1970年1月被1969年制订的《出口管理法》(the
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of 1969)取代。新的法律在名称上用"管理"(Administration)
取代了"管制"(Control),表明随着国际形式的缓和以及在工商界的要求下,美国开始
放宽对出口的限制。但是在冷战环境下,美国的出口管制并没有真正放松,反而还有所强
化。例如1974年通过的两项修正案赋予国防部审查和否决两用技术产品出口的权力。
1979年10月,经过激烈的争论,美国国会又颁布实行了一部新的《出口管理法》(the
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of 1979,以下简称1979年法)。 在经历了70年代经济危机和
贸易逆差的情况下,美国工商界纷纷游说国会,攻击政府的管制政策。在商界的巨大压力
下,这部法律提出了压缩管制产品范围、改进审查手段、提高许可证审批效率等要求,以
方便和鼓励美国商品,尤其是具有竞争力的技术产品的出口。
但是在里根政府上台,美国推行对苏联的"新冷战"政策,在出口管制问题上不仅没
有出现松动,反而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措施。与此同时,美国在80年代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
贸易赤字现象,这就引起了美国企业的严重不满。1987年3月,美国国家科学院提出的一份
报告认为,美国目前的出口管制体系过于严厉,超过了必要的程度:"虽然出口管制是为
了国家安全,但目前过于严格的出口管制严重削弱了美国技术产品在国外的竞争力,以至
于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削弱了国家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1987年开始的美国第100届国会决心采取行动改变美国贸易严重逆差的
状况,其结果是通过了1988年的《综合贸易竞争法》(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这部法律的重点是对1979年的《出口管理法》提出了修正,要求放宽对装
有微电脑的科学和医疗仪器的出口;压缩单边管制的规模;缩小对转口产品的出口限制等
等。 为了有效贯彻这部法律,提高出口管制政策的透明度,美国商务部制订了相应的《出
口管理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详细列出有关出口管制的各项政
策规定,提供办理出口许可证的综合指南。作为一个出口指南,美国商务部每周都会在"联
邦纪事"(Federal Register)上公布这个条例最新修改和变化。
1989年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冷战终结。就在此时,
1990年9月30日1979年的《出口管理法》10年有效期满,宣布到期。然而由于朝野各界在出
口管制问题上出现的严重意见分歧,加上国会与行政部门之间的斗争,美国至今仍没有产
生取代它的新法律。为了应急,当时的布什总统发布行政命令(总统行政令第12730号)规
定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the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授
权范围内继续实行1979年法的有关条款。 此后,克林顿总统也使用同样的方式两次延长了
该法的生效期。在这段时间里,国会和行政部门之间依然没有解决它们在出口管制问题上
的分歧和争执,因此始终没有批准取代1979年法的新法律或者修正案。这样到了1994年8月
20日,1979年法经过三次延期后正式寿终正寝。不过,根据克林顿颁布的行政命令(总统
行政令第12924号),1979年《出口管理法》终结后,《出口管理条例》在《国际紧急经济
权力法》授权的范围内继续执行。
除上述国内立法之外,规范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还有一系列国际多边出口管制组织和
条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多边出口控制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Mutilateral Export Control,COCOM),即著名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
这个组织成立于1949年,在冷战背景下它是西方对苏联社会主义集团推行技术封锁政策的
核心机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巴统"是美国约束西方盟国对社会主义阵营技术贸易的
得力工具,同时它也成为统帅冷战时期美国技术出口管制政策的主要标准之一。"巴统"
的出口管制项目主要有三份清单,国际原子能清单、国际军火清单和工业清单,涉及民用
项目和"两用"技术产品的项目主要包括在工业清单内。"巴统"推行的是一套十分的严
格的管制程序,任何成员国的出口许可都需得到其他成员通过投票方式的审批。
随着柏林墙倒塌、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终结,"巴统"的使命也宣告基本终
结。为了便于向发生巨变后的东欧各国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兑现西方在"和平演变战略"
中许下的承诺,1990年5月美国首先向"巴统"提出建议,要求大规模削减管制项目的数量
和管制国家的范围。1993年10月,美国再次向"巴统"提出建议,要求逐步解散这个组织,
组建新的多边技术管制机制。 这个建议很快就得到了其它成员国的同意。1994年3月31日,
"多边出口控制统筹委员会"正式宣告停止一切活动,这个冷战时期与北约齐名的经济组
织随着冷战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
1996年9月,在"巴统"解散两年之后,诞生了一份名为《关于常规武器与两用产品和
技术出口控制的瓦瑟纳尔协定》(Wassennar Arrangement,简称"瓦瑟纳尔协定")的文
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多边出口控制机制。参加该机制的国家有33个,除了原"巴统"
成员国外增加了一些前苏东国家。"瓦瑟纳尔协定"的"基本"项目清单与1993年"巴统"
放松管制后的清单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与"巴统"相比,"瓦瑟纳尔协定"是一个十分松
散的组织。它没有正式列举被管制的国家,只在口头上将伊朗、伊拉克、朝鲜和利比亚四
国列入管制对象。设在奥地利维也纳的秘书处也不具备审议职能,也就是说不要求成员国
的出口许可证送交秘书处通过其它成员国的审议。
"瓦瑟纳尔协定"的成员国可以参照共同的管制原则和清单自行决定实施出口管制的
措施和方式,自行批准本国的出口许可,这就是所谓的"自行处理"(national discretion)
原则。该协定比较有约束力的是所谓的"不破坏协议"(no undercut agreement),意思
是如果一个成员国向协定秘书处提交关于某个项目禁止出口的报告,那么其它成员国在批
准同类项目出口时应当首先向该国征求意见。 因此在总体上,"瓦瑟纳尔协定"与其被认
为是一个多边出口管制协定,不如说是一个关于出口管制的国际意向书,并不具备实际控
制力。
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概况
现行美国出口管制政策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管理民用项目,重点是所
谓的"两用"项目("dual-use"items),即既可以用于民用目的,也可以用于军用目的
的技术和产品的出口。管制该项目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出口管理法》以及根据本法制定的
《出口管制条例》商务部主要负责这类项目的管制,尤其是商务部下属的出口管理局负责
具体的政策实施、政策协调和出口许可证审批等工作。第二部分主要管理军用项目
(munitions items),即武器、军火和防务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输出。《武器出口控制法》
(Arms Export Control Act)是管理该项目出口管制的主要法律。这类项目的审批主要由
国务院负责,具体的负责部门是国务院国防贸易控制办公室。
根据修改后的《出口管理法》(1979年)通则的规定,在"管理出口、提高出口管理
效率、以及最大限度减少干预参与商业活动能力"的宗旨前提下,美国出口管制的产品和
技术范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1、限制那些会大大增强任一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军事潜力,从而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产
品和技术出口;
2、限制那些为有效促进美国对外政策或履行公开宣布的国际义务而必须限制的产品技
术出口;
3、限制那些为避免国内经济出现原料过分匮乏、减少国外需求引起的严重通货膨胀影
响而必须限制的产品出口。
上述三个方面的管制范围也反映出了美国出口管制的主要目标,简单而言即维护国家
安全、促进对外政策和控制商品短缺。所谓控制短缺商品指的是,为了避免国内经济由于
过度国际需求而出现通货膨胀、原料匮乏等现象而采取管制措施,管制的主要有铜、兽皮、
核桃木、原油、西洋红杉等初级原材料产品。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管制只偶尔或短
暂实施过,因此在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中并不占主要地位。相对而言,国家安全和外交政
策的需要在美国的出口管制中占据了重点。
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主要管制的是战略物资和技术资料的出口,防止这些资源流向
所谓的"令人担心"的国家。在决定受管制国家名单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有:一、该国所奉
行政策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二、该国是否社会主义国家;三、该国与美国现存及潜在
的关系状况;四、该国与美国的盟国及敌国现存和潜在的关系状况;五、该国的核能力和
遵守核控制的情况;六、该国再出口控制的能力;七、总统认为需要考虑的其它因素。 在
1979年法"限制出口国家名单"当中列举有32个受管制国家,其中包括中国。根据规定,
所有因国家安全原因管制的美国产品和技术,无论是从美国直接出口,还是从第三国转口,
都受将受到严格限制,并且严格禁止这些国家将进口的美国民用技术转为军事用途。
在促进对外政策方面,出口管制主要服务于加强和推进美国的对外政策,履行美国承
诺的国际义务,重点包括打击国际犯罪和恐怖活动、控制核生化导弹技术的扩散、促进人
权保护以及保持地区稳定等内容。由于对外政策管制的目标和衡量标准不象国家安全管制
那样明确,比较容易引起国内意见分歧和矛盾冲突,所以在决定实施管制的时候通常需要
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可行性,管制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二、一致性,管制是否
与既定外交政策相协调;三、能力,管制能否有效执行;四、经济影响,管制对美国的出
口、国际竞争力、国际信誉以及对国内企业、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五、外国政府可能的
反应。 美国政府在决定这个方面管制政策时受国内、国外因素的影响比较大,尤其是根据
《出口管理法》(1979年)修正案的规定,总统必须向国会报告管制的性质、内容、执行
情况和结果。(1988年修正案)
冷战时期,根据国家安全、对外政策和短缺控制的需要,美国的出口管制制定有不同
的国别政策。《出口管制条例》将除加拿大之外的所有国家分为七个组。(除少数情况外,
加拿大可以获得同美国国内一样的待遇,因此列在所有组别之外)由严格向宽松依次是:Z
组,出于外交政策原因实行全面禁运的国家;S组,出于国家安全、反恐怖、不扩散和地区
稳定需要,除药品、医疗用品、食品和农产品外全面管制的国家;Y组,允许非战略物资出
口,但出于国家安全需要,禁止任何涉及军事用途、有助于提高军事能力、有损于美国安
全的商品和技术出口;W组,基本原则同上,但管制范围更宽松;Q组,基本规定同上,限
制更少一些;T组,总原则和政策同下述的V组,但对刑侦设备、军用设备进行许可证管理;
V组,除上述组别外其它基本不存在管制的国家,但依据具体情况和政策,该组各国并不享
受同等待遇。 当然这种组别的区分不是一成不变的,依据现实情况的变化,列入各组的国
家名单随时都会发生变化。冷战结束后,这种组别划分的方法虽然没有被取消,但是内容
和实际执行方面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
实际负责两用技术出口管理的是美国商务部出口管理局。该局在收到出口商提交的出
口许可证申请后,根据所申请的内容酌情转送国务院、国防部、能源部、军备控制与裁军
署、中央情报局等相关部门审批。如果各部门之间出现意见分歧,则提交给由各部门人员
参加的出口咨询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分三级组成,第一级是行动委员会,第二级是咨询委
员会,第三级是管理审查委员会。通常情况下该委员会都以多数表决的方式决定问题,如
果意见分歧不能圆满解决就逐级上报;如果出口咨询委员会内无法解决分歧,那就只好送
进总统办公室。根据1995年12月5日的总统行政命令,所有出口申请都必须在90天内完成审
批程序。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被划入美国出口管制的Y组,两国还保持有一定
的贸易往来。但一年之后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当年12月2日美国商务部宣布
中国为"敌对国家",列入全面禁运的Z组,禁止美国的一切出口,禁止美国船只停靠中国
港口,限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952年巴统成立专门的"中国委员会",形成所谓的"中
国差别待遇",使巴统对中国的禁运项目两倍于对苏联的管制。在此后20年里,中美贸易
差不多完全断绝。
1969年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之后开始着手缓和中美关系,作为美国向中国发出的和解
信号的一部分,美国也开始逐步解除对中国的贸易禁运。1969年12月9日,美国宣布允许美
国商人同中国进行非战略性货物贸易,此举宣告美国对华"禁运"政策的终结。1971年6月
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可以向中国出口的非战略性物资清单,喷气飞机和高级计
算机等两用产品不包括在内,但可以以逐项审批的方式发放出口许可证。一个月后,基辛
格成功地实现了对中国的秘密访问,中美贸易解冻的步伐大大加快。1972年春,美国商人
出现在广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不久,中国被重新列入Y组,与苏联东欧大部分国家
享受同等待遇,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享受着美国和巴统偏向性的优惠。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中美关系走上正轨的过程中,技术出口管
制问题一直是双边关系中十分重要的议题之一。1月30日,邓小平在访问美国时与卡特总统
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这是中美建交以来最早签署的双边政府协定之一,由此开辟了
中美科技交流和贸易往来的新时期。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在意识到落后和差距的情况下,对国外先进科技的学习引进成为中
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在这种状况下,美国的出口管制成为干扰中美经贸发展的障碍。
中国的开放也为美国企业和商家提供了十分巨大的市场机会,在进入这个市场的过程中美
国企业也感到过于严格的技术管制措施约束了它们的竞争能力。
但在美国国内,反对放松对华出口管制的意见依然占有很大的分量。这其中有顽固的
意识形态考虑,认为不应该放松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管制;也有战略思想上的分歧,
认为不应该过分重视中国而忽视与苏联的缓和;此外还有外交上讨价还价的考虑,企图以
放宽管制为筹码换取中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的让步。 因此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美关
系中,对华出口管制问题构成了美国国内政策争论和两国外交斗争的焦点之一。
面对70年代后期苏联咄咄逼人的战略进攻态势,美国越来越迫切地意识到"大三角关
系"内中美战略合作的重要性。中美在共同对付苏联时的安全和军事合作需要构成了美国
在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随着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事件,
"联华制苏"的战略利益占据了上风,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在管制问题上的松动。1980年4月
25日,卡特总统宣布将中国从Y组划出,列入专门为中国设立的P组。在这个管制类中,中
国作为"非敌国"原则上可以获得美国的军民两用技术和产品。但是对中国的技术出口还
必须通过逐案审查的方式,并且附有严格的限制条件,因此还是不能满足中国方面需要和
美国企业的要求。
面对对华管制问题上依然存在的问题,里根政府上台后首先采取了"双倍政策"(Double
Threshhold Policy)的解决方法,即允许向中国出口的技术和产品的技术水平可为向苏联
出口的两倍,同时简化出口审批的程序。随着中美关系逐渐走向稳定成熟和顺利发展,美
国最终于1983年6月21日宣布,从当年11月23日开始把中国提升为"友好的非盟国"待遇,
列入同西方国家、中立国和印度、埃及等发展中国家并列的V组,"强调向中国出售技术与
产品应该象美国向其它友好国家出售一样自然"。
美国在对华管制上的逐步宽松,一方面反映了美国自身战略和经济利益的需要,另一
方面也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和积极的外交努力的结果。邓小平同志在接见美国客人时多次
谈到过技术转让和出口管制的问题,亲自做美国人的工作。1983年8月28日,他在会见美国
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时指出,中美关系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台湾问题;一是技术转让。
在技术转让问题上,美方有些松动,我们表示欢迎。但松动到什么程度,也还要看。 在这
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还表现出他特有的灵活现实的外交风格,在建交之初的1979年,他在
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科技部主任休伯曼会谈时对中国被置于同苏联同等的Y组表示不满,
同时提出了一个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法,即在26个英文字母中另选一个给中国的出口级别。
这就是后来给中国单独开列的P组的由来。
1983年11月,中美签署关于美国向中国转让技术的有关文件,美国政府正式发表"对
华出口指导原则"并修改了《出口管理条例》中有关中国的条款。但是V组作为一个混合大
组,其内部各个国家并不享受同等的待遇,因此中国享受的技术转让仍然有很多的限制。
正如美国商务部公告中同时指出的:"这一变化将允许对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某些产品和
技术实行限制,而且对中国的出口仍然要接受安全审查。" 具体而言,美国将对华出口的
技术和产品分为三类:
一、绿区(Green Zone):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比较小的技术和产品,商务部有直接
审批权,一般不需要跨部门审查。这一大类约占总数的75%。
二、黄区(Yellow Zone):属高级技术范畴,但低于红区水平的技术和产品,需要经
过国防部及其它部门参与逐项审查。
三、红区(Red Zone):最先进的技术,能直接用于尖端军事系统,对美国国家安全
构成显著威胁的技术和产品。这类项目甚至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国也不能分享,所以拒绝向
中国出口。
1985年9月,巴统达成一项简化对华出口审批的协议,接受美国提出的绿区标准,并且
将数量从7项扩大扩大到27项,条件是中国政府承担出具"最终用户证明"和提供担保的义
务。中国于同年11月接受这个条件,责成对外经济贸易与合作部技术进出口司具体承办。
为了方便出口商的对华出口申请,美国商务部出口管理局于1986年12月成立了专门的"中
国科",至此美国新的对华出口管制体系基本成型。此后直至1989年6月,美国和巴统还先
后五次调整和放宽了对华出口管制绿区的范围和标准。在宽松的管制政策下,1988年中美
高技术贸易达到顶峰,根据美方统计,当年申请对华出口的报告共6900份,总额36亿美元,
其中91%获得批准,出口额达30亿美元;只有1.25%被否决,其余的或者无需出口许可,或
者是资料不全等技术原因未获批准。
1989年在北京发生的"六四事件"极大地冲击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双边技术交流和贸
易更是首当其冲。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美国政府首先宣布暂停两国已经达成的几项军
事技术转让合同。接着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对华制裁措施,其中包括禁止治安类技术和产
品的出口、中止长征火箭发射休斯卫星的合同、禁止出售核设备和核燃料等等。根据美方
资料,美国政府当年至少中断了300项对华出口的许可。 在国会的巨大压力下,美国政府
还宣布停止进一步放松对华出口的管制。此后美国单方面的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基本上陷入
了停滞,但是由于冷战结束的局面,巴统大大放宽原有的管制措施并且最终宣布解散,这
也间接地也放松了很多对中国的出口限制。由于美国和西方对华制裁的失败,以及巴统的
解散,从1995年开始,中美之间的技术贸易又出现了明显的回升势头。1995年当年中国技
术进口合同金额比上一年增加了3倍多,合同数量增加了8倍;其中从美国引进的合同金额
增加了将近4倍,合同数量增加了10倍多。
在上述基本情况之外,美国还经常在人权、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等问题上动用技术贸
易制裁的手段,给中美关系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发生在不扩散问题上的
三次争端。一是发生在1987年的所谓中国向伊朗出售"蚕式导弹"事件;后两件是先后发
生在1991年和1993年的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所谓M-11型地对地导弹事件。在这些事件中,
美国都以其一面之见,单方面宣布采取高性能计算机、发射卫星等技术管制制裁。而美国
的制裁在事实和法律上都很难立足,因此这种单边性的行为只能孤立美国自己、损害美国
企业的利益。 最近的例子有1999年美国政府借口中国解决"法轮功"事件侵犯宗教自由和
人权,宣布对出口中国的刑侦产品实行管制。
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出口管制是美国为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外交政策所凭借的经济手段之一,其核心是政
治与安全的需要。因此,在中美关系的层面上,出口管制问题直接决定于两国关系的总体
状况,正象邓小平指出的,"在技术转让问题上,重要的是中美能成为什么样的朋友,是
普通朋友,还是比较好的朋友"。 反过来看,出口管制政策的变化也能够反映出美国对华
战略态势的变化。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员伊文*费根鲍姆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在1996
年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导弹演习三年后,高技术问题已经逐渐取代人权,成为目前高度政
治化的美国对华政策辩论和关注的中心", 近来在美国国内发生的以"考克斯报告"为代
表的一系列事件已经证实了上述判断。这种"中心化"的趋势导致美国对华的出口管制有
所加强。 而且从目前情况看来,高技术和美国出口管制问题还可能进一步成为影响两国关
系的焦点问题。
首先,中美关系正在面临一个重新定位的过程。在经历了七八十年代战略三角关系之
后,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始终处在不断调整定位的起伏之中,随着中国经济和综合实力的稳
定提高,美国决策者已经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中国可能成为其潜在的唯一战略对手。这种
忧虑促使其开始采取一系列防范性的措施,技术管制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其中最受关注的手
段之一。其次,技术管制问题的特殊性质使它很容易被国内政治斗争所利用。高技术本身
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并通常带有保密性,因此普通百姓一般很难明辨是非,而此类问题又
往往戴着"涉及国家安全"的大帽子出现,很容易制造骇人听闻的视听效果。这也正是考
克斯之流能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最后,美国现存的出口管制体制存在缺陷。在最后一部
出口管理法1994年终结后,美国的出口管制体制实际上处在某种"群龙无首"的状态,这
使国会和利益集团容易取得发言权,使问题更加政治化和敏感化。
不过,作为美国推行外交政策的手段,出口管制政策的有效性始终受到一系列因素的
制约。在冷战后的环境下,这些因素变得更加突出,从而使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充满着内
在的矛盾和冲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政治目的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出口管制事实上是以牺牲美国的部分出口利益
为代价来追求某种政治和安全利益,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常常成为美国出口管
制政策争论的中心。在当今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中,高技术是美国经济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之
一,但由于美国推行严格的管制政策,这个优势并没有在中美双边贸易中表现出来。中国
在技术贸易领域始终处于净逆差的状态,1997年逆差达104亿美元,但中国引进技术的
37.35%来自欧洲,21.29%来自日本,17.61%来自加拿大,美国只占11.4%。 这种状况显然
与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科技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1997年中美双边贸易美国的逆差163.92亿
美元,而对华技术合同出口额仅18.16亿美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美国政府在
技术出口方面制造了过多的政治性障碍。
二、单边性管制与国际技术市场竞争的矛盾。事实上除了少数尖端技术之外,美国管
制中的大部分产品和技术并不具备垄断性。日本、西欧、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掌握着很多
可替代的先进技术,而且在经济或其它利益的驱使下愿意向外转让和输出。即使在冷战时
期,存在巴统这样严格的多边管制机制的情况下,英日等国向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先进技术
的情况也屡有发生。巴统解散后,后继的"瓦瑟纳尔协定"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架子,更加
难以约束所谓"盟国"的行为。技术来源的多源化使美国单方面管制的效果大打了折扣,
而且在激烈竞争的技术市场上使美国企业处于不利地位,反过来也增加了美国国内反对管
制的呼声。
三、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与管制标准之间的冲突。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日
新月异的快速进步和发展,而出口管制的官僚程序经常很难跟上技术水平提高的步伐,滞
后的管制标准和发展的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经常会引发出口商和政府之间的矛盾。高性能
计算机技术问题最典型地反映了美国出口管制的尴尬处境,1992年5月美国界定对华出口高
性能计算机的最高限度是195MTOPS(理论运算百万次/秒),1994年提高到1,500MTOPS,1996
年提高到7,000MTOPS,1999年7月1日最新公布的标准是12,300MTOPS。 在短短7年中这个标
准提高了60多倍,而专家指出这种修正依然很难适应所谓"穆尔法则"的要求,英特尔公
司创始人之一戈登*穆尔创造的这项法则认为,计算机微处理器发展的速度是每18个月翻
一番。
最后,对中国而言,技术引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短差距,降低技术改造的成本,提
高经济发展的效率,但这种引进的手段毕竟是有限度的。国家高科技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在
根本上只能立足自力更生的原则,这是新中国50年科技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也是在改革
开放条件下中国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在本文对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研究过程中,这一点
题外话却是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感受。
1999年12月31日
Export Control Act of 1949; United States Code (Washington: Government Office of Printing, 1989, 以下简称
U.S.C.), Title 50, sec. 2021-2032.
Ibid.
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of 1979, as amended; U.S.C., Title 50 app. Sec. 2401-2420.
"Overview of the Export Administration Program", March 1987,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 S. A..
Omnibus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 Public Law, 100-418, August 23, 1988, U.S.C., sec.5021.
Public Law 95-223, 91 Stat. 1628, U.S.C.Title 50 sec.1701-1706.
"Toward a National Export Strategy: Repor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Trade Promotion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ep. 30, 1993.
参见www.bxa.doc.gov/Wassenaar/Initial Elements.htm
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of 1979, as amended; U.S.C.Title 50 app. Sec. 2402(2).
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of 1979, as amended; U.S.C.Title 50 app. Sec2404(b).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part 772, definition of "control country".
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of 1979, as amended; U.S.C.Title 50 app. Sec.2405(b).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part 772, definition of "control country".
《人民日报》,1981年6月11日。
"Background Paper on U.S. Export Licensing Policy for the P.R.C," Export Administration Annual Report
Fiscal Year 1983, March, 1984.
《邓小平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的谈话》,1983年8月28日,转引自宫力:《峰谷间的震荡:
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133页。
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49.
"Background Paper on U.S. Export Licensing Policy for the P.R.C".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sec. 738.2.
Export Administration Annual Report Fiscal Year 1988, March, 1989.
Export Administration Annual Report Fiscal Year 1989, March, 1990.
国家统计局、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8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年),第201-202页。
朱明权:《事实、法律和联系问题:美国的对华制裁以及撤消》,谢希德、倪世雄编:《曲折的历程
--中美建交20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44页。
宫力:《峰谷间的震荡》,第133页。
Evan A. Feigenbaum, "Who's Behind China's High-Technology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1 (Summer 1999), p.95.
例如美国第106届国会通过的《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中有多处条款涉及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调整,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00, Public Law 106-65(s 1059).
课题组:《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1998年)》,(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第137页。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8年)》,第202页。
"Export Controls on Computers",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July 1, 1999
转引自Select Committee of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Military/Commercial Concer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541.